第457章 罪狀
湜道:「還能如何?終究是胳膊擰不過大腿,明知結果的事情,掙扎有何意義?」
他這話也透著幾分無奈。
韋家在他人面前確實高高在上,可跟李治這皇帝一比,卻與常人沒什麼兩樣。
李崇德一想也對,面對強硬的皇帝,他們向來的風格不正是一退再退,將寶壓在未來,而不是頭鐵的選擇跟皇家硬碰硬。
「此事無法挽回,強求不來。婁師德此人你們調查過沒有,可有什麼背景?此例不可開,若養成此風氣,對我等都不好!」
懸報館存在的隱患,他人未必不知,只是牽扯了太多的利益。
豪門世家不敢正面與皇家對抗,可合力打壓孤立某一官吏卻是能做到的。
他們一旦出手,通常針對的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族人。
影響的不是一個人的仕途,還會牽累全族人的未來。
在這個宗族思想極重的時代,這是很致命的。
韋湜道:「鄭州原武人」
李崇德心想:「地方庶族罷了,最好對付。」
「貞觀十八年,婁師德進士及第」
李崇德再次心道:「貞觀年的狀元,不算什麼。」
在陳青兕推行科舉改革之前的狀元,與之後的狀元是不同的概念。
反而證明婁師德沒有很深的人脈,真要有人脈,那時代誰考科舉。
「當任江都尉十年,兩個月前才得到晉升,進京赴任。」
李崇德臉上透著一副死定了的表情,笑道:「原來是個譁眾取寵之輩」
在他的眼裡,婁師德這樣沒身份沒背景,在一個地方苦幹十年,才靠著資歷混出頭的官吏,然後一朝得勢,就覺得自己能夠在廟堂上翻雲覆雨,靠著滿腔熱血,橫衝直撞之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嫩頭青,譁眾取寵之徒。
對付這種人最是簡單不過了
韋湜並沒有說完,又加了一句:「他跟陳尚書關係密切。」
李崇德立刻接話:「難怪有底氣!」
接著就不說話了,態度完全來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
韋湜見狀笑了笑,有心朋友間調侃兩句,話還未出口,卻自嘲一笑,自己又有什麼資格取笑?
陳青兕現在如日中天,即便是許敬宗這樣的宰相都不願與之為敵。
他的護著的人,誰敢動?
他們韋家的老祖如果不想對婁師德下手,就不會將對方的一切事跡調查的如此清楚,如果真敢亮劍,也不至於至今一點消息也沒有。
韋湜道:「事不可為,人又動不得,認命吧!」
熬走了太宗李世民,來了一個李治,死了一個李義府,又有一個更加厲害的陳青兕
這寒門哪來那麼多可怕的人物?
這莫名想到李義府,李崇德突然打了一個寒顫,即便知道李義府死了,可一想著他,還是忍不住發怵。
也不知什麼時候是頭
李崇德又與韋湜聊了許久,然後告辭離去。
李崇德喝了不少的酒,有些醉意,但還是先將自己探來的消息告訴了李家在長安的管事。
如果他想像中的一樣,得知婁師德背後站著陳青兕,馬上沒有了下文。
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在婢女的侍奉下洗去了身上的酒意,獨自前往書房靜讀。
溫故而知新,即便是他們,也需堅持不懈的讀書來維持自身文化水平,維繫競爭力。
這一抵達書案前,眉頭忍不住皺起:他的書案上放著一份折書。
李崇德不喜他人打擾他讀書,也不喜外人進他書房,除了需要曬書的時候,允許下人進書房幫忙,其他時間寧願自己動手打理,也不想外人動自己的書。
現在這案几上莫
 末世大回爐 喪屍爆發,人類絕境來臨,地球磁場瞬變,一切回歸最初,回到原始。 末世,我來了。 ———————— 初級1群:424355442(已滿)。 初級2群:582138519。 正版VIP群
末世大回爐 喪屍爆發,人類絕境來臨,地球磁場瞬變,一切回歸最初,回到原始。 末世,我來了。 ———————— 初級1群:424355442(已滿)。 初級2群:582138519。 正版VIP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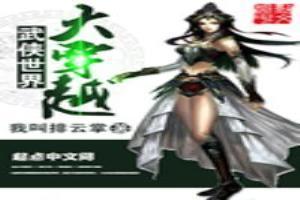 武俠世界大穿越 一位武學天賦極高的現代散打高手,穿越於各類武俠世界中,一步步成為顛峰強者的故事!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武俠世界大穿越》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
武俠世界大穿越 一位武學天賦極高的現代散打高手,穿越於各類武俠世界中,一步步成為顛峰強者的故事!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武俠世界大穿越》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
 萬界聖師 ps:新書《宿主請留步》已上傳,一個發生在不小心玩炸了系統之後,主角翻身做系統的故事。 本書簡介:從今天起,做一個光榮的人民教師。 瞎搞、裝逼、調教主角徒弟! 從今天起,關心萬千世界會不
萬界聖師 ps:新書《宿主請留步》已上傳,一個發生在不小心玩炸了系統之後,主角翻身做系統的故事。 本書簡介:從今天起,做一個光榮的人民教師。 瞎搞、裝逼、調教主角徒弟! 從今天起,關心萬千世界會不- 我全家都是穿來的
- 殯儀館的臨時工
- 大漢科技帝國
- 魔法種族大穿越
- 不朽星空
- 末日之火影系統
- 九星毒奶
- 修真四萬年
- 財務自由後,她們獻上了忠誠
- 死神:沒有外掛,投靠藍染
- 速通修仙!
- 嫡女歸來,皇叔助我奪江山
- 我的諜戰日記
- 武動之真正的武祖
- 不科學御獸
- 我!天道,讓地球成就萬界至高
- 全民深淵:我技能無限強化
- 趙旭李晴晴
- 和前世宿敵成親後(雙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