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往昔.除夕
李惑病得更重了。渾身疼痛,遍體生寒,躺在床上動不了一點。
梅瑾萱一摸,果然在發熱。
又去延請太醫,沒想到這回連景陽宮的大門都出不去。
德妃得到消息,派了太監把景陽宮前門側門把持得死死的,放話任何人不得進出。
饒是他們怎麼哀求也不肯讓開,還作勢要打他們。景陽宮其他人不想挨打,紛紛後退,只留下梅瑾萱這麼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再想堅持,也沒得任何辦法。
現在三個時辰過去了,李惑的身體越來越燙,人也越來越不清醒。
早些時候還能回應兩句,現在除了喊冷,再說不出別的話。
梅瑾萱抱著他,一顆心仿佛被放上了烤板,又急又慌。眼見著,懷裡的人連「冷」都喊得少了,似乎就要徹底死去。梅瑾萱一顆心揪在一起,眼淚不由自主地盛滿了眼眶。
但下一刻,她抬手把即將落下來的淚水擦乾。
她的眼神變得堅毅,決絕。
前面算得上「倒霉」二字的人生教會了她一個道理——哭泣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
只有行動,行動才能化解危機,讓自己活下去。
於是,梅瑾萱從人事不省的李惑身下抽回手,為他輕輕地掖了掖被角。然後,穿好外衣,大步走出寢殿。
外面,曾經領著梅瑾萱熟悉環境的宮女姐姐青櫻正守著,見到梅瑾萱出來,快步上前詢問:
「殿下怎麼樣了?」
梅瑾萱沉默地搖了搖頭。徑直走向景陽宮正門。
「誒!你幹什麼去!現在不能出去!」
看到梅瑾萱的行動方向,青櫻好心去拉她。
但是梅瑾萱卻堅定地推開了她的手,毅然拉開了那扇朱紅的大門。
吱嘎。
隨著那黑漆漆的一條線,逐漸變亮,拉寬,兩個高大魁梧的太監立在門口,聽到響動立時看過來。
他們穿得和其他宮人無太大差別,冬天奴婢多穿灰藍色,但今夜是除夕,宮女們可以穿玫紅,而太監們則穿絳紫,看起來一片喜氣洋洋。
不過穿得再吉祥,也蓋不住他們幹得不是人事。
「幹嘛!不都說了,不許出入。」
一人低頭看著剛到他腰的梅瑾萱,瞪著眼睛,表現出非常明顯地恐嚇。
梅瑾萱咽了下口水,沒有退縮。
「四,四皇子,病得厲害。他要是真有什麼閃失,你,你們擔待得起嗎?」
她結結巴巴的樣子沒有任何威懾力,反而引起一陣鬨笑。
梅瑾萱又氣又羞,紅了臉,咬牙繼續說:
「你們今日這樣攔著我們去找太醫,若是被陛下知道了,你,你們也不會有好下場的。依照宮,宮規,得杖斃!」
沒想到,提起宮規,兩個太監笑得更大聲了。
好半晌,他們才停下來,一個人不懷好意地走近梅瑾萱,不屑地捅了下她的腦袋,那力氣瞬間讓梅瑾萱踉蹌一步,向後摔倒。
太監嗤笑一聲:「你是今年新來的宮女吧?我好心教你一次,現在這後宮裡,德妃娘娘就是規矩!德妃娘娘說,四皇子是病重醫治無效死的,那他就是!沒人會管,到底有沒有太醫來看過,也沒人會知道咱們兄弟今天到底是這景陽宮門口守著,還是得了假找個地方喝酒去了。懂?」
梅瑾萱氣得渾身發抖。但她更多的是覺得荒唐。
在她之前的認知中,皇權就是這世間至高無上的存在,讓誰生就生,讓誰死就死。可沒想到,一個皇子,帝王的血脈,在這皇宮裡卻可以被這樣糟踐,連一個最低等的太監都能拿捏他的生死。
德妃的狗上個月噎了骨頭,還請了四五回太醫去瞧呢。而李惑,只能孤零零地躺在床上,連見一面太醫都不行,唯有等死。
正應了那句話——活得連條狗都不如。
梅瑾萱坐在地上咬緊牙關,淚水在眼睛裡打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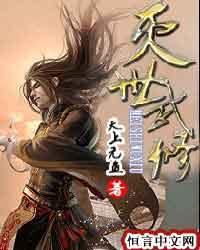 滅世武修 一條枷鎖,鏈住萬千星域。一顆心臟,沉浮黎明破曉。…………無數位面大陸,宗門林立,站在絕巔者,可笑蒼天,瞰大地。本是一代神體,卻得滅世傳承,是沉淪殺戮,還是走上巔峰之道?且看烏恆如何抉擇…………
滅世武修 一條枷鎖,鏈住萬千星域。一顆心臟,沉浮黎明破曉。…………無數位面大陸,宗門林立,站在絕巔者,可笑蒼天,瞰大地。本是一代神體,卻得滅世傳承,是沉淪殺戮,還是走上巔峰之道?且看烏恆如何抉擇………… 錦衣春秋 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地藏捲軸突現世間,黃金鳳凰再臨天地,南北爭雄,密雲重重。深宮詭虞,疆場喋血。以天地為棋盤,眾生為弈子,英雄豪傑,風月美人,演一出曠世棋局!本書官方群:70016
錦衣春秋 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地藏捲軸突現世間,黃金鳳凰再臨天地,南北爭雄,密雲重重。深宮詭虞,疆場喋血。以天地為棋盤,眾生為弈子,英雄豪傑,風月美人,演一出曠世棋局!本書官方群:70016 超品相師 相師分九品,一品一重天 風水有境界,明理,養氣,修身,問道。 二十一世紀的一位普通青年偶獲諸葛亮生前的玄學傳承,沒有大志向的秦宇,只想守着老婆孩子熱炕頭,卻機緣巧合一步步走上相師之巔,成就
超品相師 相師分九品,一品一重天 風水有境界,明理,養氣,修身,問道。 二十一世紀的一位普通青年偶獲諸葛亮生前的玄學傳承,沒有大志向的秦宇,只想守着老婆孩子熱炕頭,卻機緣巧合一步步走上相師之巔,成就- 唐磚
- 抗戰之我要當團長
- 網遊之三國無雙
- 宰執天下
- 漢兒不為奴
- 武帝之天龍八部
- 偷香
- 重生之民國元帥
- 葉凡唐若雪
- 我不是老鼠
- 文豪1978
- 不放縱能叫神豪嗎?
- 妙手大仙醫
- 垂涎
- 都重生了誰考公務員啊
- 很純很曖昧
- 我在華娛當導演,寵壞天仙白月光
- 貞觀悍婿
- 從1979開始的文藝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