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2章 斷指斷姓斷親緣(3)
「……」
牧羨泉的臉上掠過一抹難堪,更加痛恨地瞪著他。
「你知不知道汪甜甜被解剖了?」應寒年從自己的大衣口袋裡取出一枚硬幣,捏在指尖靈巧地轉來轉去。
「你到底想說什麼?」
牧羨泉莫名其妙地看向他。
應寒年當空拋了一下硬幣,然後穩穩地接住,蹲在他面前,食指與中指並在一起,硬幣停在他的指尖,太陽照過,硬幣表面反射著光。
「這麼大。」
應寒年盯著他,掀開薄唇,一字一字極盡緩慢,「你的孩子,這麼大。」
應寒年說得太慢了,慢到有足夠的時間欣賞牧羨泉從莫名到猛地收縮眼瞳,牧羨泉坐在那裡,臉剎那間變白,「你什麼意思?」
不。
不可能的。
絕不可能的。
「你說我什麼意思?」應寒年笑,笑得殘忍。
「你胡說八道!」
牧羨泉難以接受,大聲地嘶吼出來,身體卻不由自主地抖起來。
「是,我是在騙你。」應寒年收斂笑意,一本正經地看著他,「無精症怎麼可能那麼好治。」
牧羨泉被他這忽來忽去的態度弄懵了,呆呆地看著他,「你到底在幹什麼?」
「可我為什麼要騙你?」應寒年又笑,「警察那邊都有法醫文件的,你可以申請來看。」
「……」
「不過,以我的手段,想造假一份文件也沒什麼難的。」
應寒年挑眉。
「……」
牧羨泉被他的手段弄得眼花繚亂,整個人像在過山車一樣,腦袋裡是空白的。
牧羨泉撲向前,一把抓住應寒年的大衣,急切地問道,「她到底有沒有懷孕?你說!你說啊!」
他喊得聲音都撕破了。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應寒年反手推開他,輕蔑地冷笑一聲,「自己猜。」
牧羨泉在應寒年的臉上根本看不出真假,腦子裡轉過太多太多的東西,轉得他不住搖頭,「不、不可能,她沒有懷孕,她不可能懷孕的。」
他怎麼可能有孩子。
他盼了那麼多年,用盡了這世上所有的先進醫學方法,一直都沒有,怎麼可能現在有!
一定是汪甜甜那個女人出軌,她出軌了!
該死的女人!
「前兩天是不是有人給你抽了血,那是我讓人去做親子鑑定用的。」應寒年從地上站起來,低眸看著他道,像是完全知道他在想什麼。
牧羨泉也想站起來,卻站不起來。
他仰頭看向應寒年,沒了恨意,只剩下鋪天蓋地的急迫,「什麼結果?」
到這一刻,他竟然是希望汪甜甜出了軌。
「是你的。」
應寒年輕描淡寫地道。
「……」
牧羨泉崩潰,雙目呆滯。
「好像不是,嘖,今天來之前才看的結果,怎麼不記得了。」應寒年勾了勾唇,慢條斯理地道。
「……」
「我忘了,抽血不是我讓人去的,那是警方的正常流程。」
他才不信什么正常流程!
牧羨泉幾乎是瘋了,上前就抓住應寒年的褲管,歇斯底里,「到底是什麼結果?孩子是不是我的?到底是不是我的?」
應寒年低睨著他,像看著一條狗,眼底儘是輕蔑的嘲諷。
良久,應寒年冷笑一聲,抬起腿一腳踢開他。
牧羨泉狼狽地往後倒去。
「要結果是嗎?這就是結果。」
應寒年說著,單手彈起硬幣,做完便轉身離開。
牧羨泉呆呆地看過去,像放慢的鏡頭,硬幣被緩緩拋向高處,又慢慢下落,折射出一閃即逝的光亮後,最後滾落在地上,一路滾進下水道蓋板中,失去蹤影。
沒了。
什麼都沒了。
不可能的,不可能,應寒年
第1002章 斷指斷姓斷親緣(3)
 他是偏執狂 他是曾經患有自閉症的總裁,在空洞的世界中,只有她能夠讓他感覺安心。因為她,他一夜之間,毀了B市最大的夜店;因為她,他拍下了一組好看的照片,轟動一時。他霸道讓她待..
他是偏執狂 他是曾經患有自閉症的總裁,在空洞的世界中,只有她能夠讓他感覺安心。因為她,他一夜之間,毀了B市最大的夜店;因為她,他拍下了一組好看的照片,轟動一時。他霸道讓她待..
 良陳美錦 未到四十她便百病纏身,死的時候兒子正在娶親。錦朝覺得這一生再無眷戀,誰知醒來正當年少,風華正茂。當年我痴心不改;如今我冷硬如刀。——————————本書已簡體出版,當當網、京東、亞馬遜均可訂購
良陳美錦 未到四十她便百病纏身,死的時候兒子正在娶親。錦朝覺得這一生再無眷戀,誰知醒來正當年少,風華正茂。當年我痴心不改;如今我冷硬如刀。——————————本書已簡體出版,當當網、京東、亞馬遜均可訂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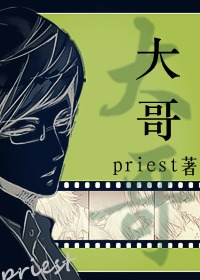 大哥 魏謙從來不知道自己老爸是誰,更不被母親待見,成天挨打挨罵已經成為了司空見慣的事,然而就這樣,他和他母親卻彼此仇視地活了下來。他十三四歲的時候,爹死娘死還帶着個只會流鼻涕的妹妹,因為無意中看到一
大哥 魏謙從來不知道自己老爸是誰,更不被母親待見,成天挨打挨罵已經成為了司空見慣的事,然而就這樣,他和他母親卻彼此仇視地活了下來。他十三四歲的時候,爹死娘死還帶着個只會流鼻涕的妹妹,因為無意中看到一- 金玉良媛
- 超凡透視
- 特種兵之利刃
- 宋朝好丈夫
- 史上第一方丈
- 清妾
- 妙手小村醫
- 我是系統之女帝養成計劃
- 那年華娛
- 四合院:開局被迫和秦淮茹換房
- 太荒吞天訣
- 龍藏
- 過河卒
- 潑刀行
- 原神:貓耳少年不會遇到病嬌
- 三國:開局截胡鄰家二喬
- 三國:臥龍姐夫,忽悠劉備搶荊州
- 從黑夜傳說開始的美影之旅
- 斗羅2:我穿成了霍雨浩的親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