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8章 當堂對質(下)
兩個證人,或者說是兩個苦主居然就在這皇城司的大堂上道出了邊家曾犯下的罪孽,而且還能拿出確鑿的物證來,這讓永王都無法憑自己身份為其開脫了,也讓他的面色愈發陰沉。
一個官員做下錯事不要緊,他很清楚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道理。但是,你做了錯事總得把善後之事都辦妥了吧,哪有留下這許多後患,等著今日被人重新提及的,這不是給自己挖坑嗎?
現在可好,光是這兩樁冤案,只要皇城司往上一報,就夠邊學道喝一壺了,更別提後面還有至少兩起案子待人證呢。這一刻,永王已經很明智地選擇放棄了,要是真攙和進去,說不定連自己都會被牽連到呢。
永王陰沉著臉陷入沉默,可呂振還沒打算停下,又一指外頭一人:「你進來說說,有何冤情。」好嘛,這下連客氣話都不說了,直接就認定他有冤了。
「大老爺,學生是為先父被邊學道這狼心狗肺的畜生害死而來!」這是個看著三十來歲,士子打扮的男人更是大聲喊冤,情緒比之前兩人還要激動。
「哦?你有何冤情,細細道來。可是你家中也有什麼田產寶物被邊家所奪,並因此害死了你父親嗎?」
「不,學生父親姓李諱巍,本是戶部一名郎中,素來小心謹慎從未出過什麼差錯。可偏偏就在十多年前,因為一次賬目出了問題,而被朝廷定罪,最終將先父與我李家三十多口發配嶺南。
「本來此事既然錯在先父,學生也是不敢喊冤的。可偏偏就在十年前,先父因在嶺南水土不服而病入膏肓時,他卻告訴了我一件當初的隱情。原來,那所謂的賬目問題根本就不是先父之錯,而是另有人犯錯,此人就是邊學道!」說到這兒,這個叫李洵的男子用滿是怨毒的眼神死盯對方。
呂振卻是立刻抓住了關鍵:「這就奇了,若真按你所言,你父當初並未犯錯,又是知情者,卻為何會甘心擔下如此重罪呢?」
這話讓李洵更是雙目泛紅,泣聲道:「皆因,皆因這邊學道實在太過狡詐。一直以來,他都表現得對我父親極其尊重,而在賬目上出了問題後,更很是慌張地向我父親求救。當時先父以為只是小事,所以便幫著做了些遮掩,卻不料,此事卻關係到朝廷數十萬兩銀子的出入,一旦查實,足夠讓任何一名官員付出慘痛代價。
「而就在先父察覺不妙,便要將事情上報時,不想這邊學道卻是搶先一步,以我父意圖貪墨國庫銀兩而篡改賬目之名將他告發……可憐我父親自入戶部以來兢兢業業,小心在意,從未出過什麼差錯,卻因一時善念反倒落得個貪污改賬的罪過。
「雖然到最後朝廷認定貪墨之事所告不實,但賬目上出了大問題的罪名卻全然落到了我父親身上,並最終嚴判流放,客死嶺南……可他邊學道呢,卻是憑此誣告得以升官,並一路做到了侍郎高位,實在是天道不公,蒼天無眼!」
直到這時候,邊學道才剛剛剛的彷徨中略略回神,此時見這士子還敢如此辱罵自己,頓時大怒,喝聲道:「簡直一派胡言,我邊學道何時害過李郎中?那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事不仔細,怪得了誰?不錯,此事確實是我告發,但那也是他咎由自取!你口口聲聲說是本官之錯,那能拿出實證來嗎?」
一件十多年前就已完全定性的案子,現在卻突然提出截然相反的說法,恐怕任誰聽了都不會相信李洵所言。不料他在面對質疑時卻並不見慌張,反倒瞪著邊學道:「我自然是有證據的。」
「什麼證據?別是你父親的什麼手札遺言吧?」邊學道冷笑,他是真不認為那起事情會留有什麼隱患。
李洵也不再遲疑,立刻從懷中取出一份紙色已枯黃的賬冊來,高舉著道:「大老爺明鑑,這就是當初他邊學道自己犯下過錯所留的賬冊,這上頭的記賬筆跡皆來自他,大可驗看,以證我所言非虛。」
「這不可能!」一見對方突然拿出這麼件證據來,邊學道都有些急了,忍不住撲將上來,似要搶奪賬冊一看究竟。
只是他才一動,身旁那些皇城司力士們也迅速
第428章 當堂對質(下)
 盛唐神話 他從小體弱多病,卻被被三軍將士奉為戰神,戰必勝,攻必取,所向無敵,他到底有何奇遇?他先是謙卑恭敬,後又專權跋扈,廢立兩代帝王,人人皆以其為操莽,然繼位之新君卻對他始終信任有加,言說永不相疑。他
盛唐神話 他從小體弱多病,卻被被三軍將士奉為戰神,戰必勝,攻必取,所向無敵,他到底有何奇遇?他先是謙卑恭敬,後又專權跋扈,廢立兩代帝王,人人皆以其為操莽,然繼位之新君卻對他始終信任有加,言說永不相疑。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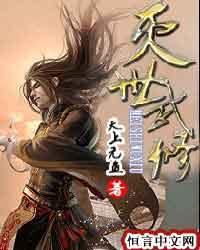 滅世武修 一條枷鎖,鏈住萬千星域。一顆心臟,沉浮黎明破曉。…………無數位面大陸,宗門林立,站在絕巔者,可笑蒼天,瞰大地。本是一代神體,卻得滅世傳承,是沉淪殺戮,還是走上巔峰之道?且看烏恆如何抉擇…………
滅世武修 一條枷鎖,鏈住萬千星域。一顆心臟,沉浮黎明破曉。…………無數位面大陸,宗門林立,站在絕巔者,可笑蒼天,瞰大地。本是一代神體,卻得滅世傳承,是沉淪殺戮,還是走上巔峰之道?且看烏恆如何抉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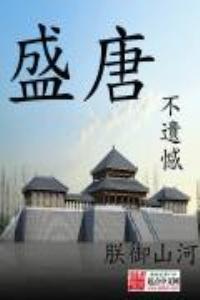 盛唐不遺憾 沒有屈辱和遺憾,只有勝利和輝煌。 鐵軌鋪向哪裡,大唐的利益就延伸到哪裡。 火炮戰車所向無敵,一帶一路再創輝煌。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盛唐不遺憾》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
盛唐不遺憾 沒有屈辱和遺憾,只有勝利和輝煌。 鐵軌鋪向哪裡,大唐的利益就延伸到哪裡。 火炮戰車所向無敵,一帶一路再創輝煌。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盛唐不遺憾》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 三國重生馬孟起
- 大明最後一個狠人
- 網遊之三國無雙
- 超級兵王
- 花豹突擊隊
- 漢兒不為奴
- 贅婿
- 貞觀大閒人
- 財務自由後,她們獻上了忠誠
- 死神:沒有外掛,投靠藍染
- 速通修仙!
- 嫡女歸來,皇叔助我奪江山
- 我的諜戰日記
- 武動之真正的武祖
- 不科學御獸
- 我!天道,讓地球成就萬界至高
- 全民深淵:我技能無限強化
- 趙旭李晴晴
- 和前世宿敵成親後(雙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