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教頭快刀,熊鷹虎豹
「你這娃兒,總想挑最上進的那條路。
老夫年輕的時候,也像你這般心高氣傲。
很難說清,這究竟是好是壞。
因為若不想著爭口氣,老夫這輩子,興許就甘於做賤戶賣苦力了。
哪有後來風光的時候。」
對於白啟的回答,梁老實好似已經猜到,笑呵呵說著。
他瘦小的身子靠進那張搖椅,腿腳蓋著保暖的毛毯。
抬手指向停泊烏篷船、小舢板的碼頭埠口:
「你也知道,黑河縣沒有官府衙門。
咱們是鄉下地方,難進郡城的法眼。
這裡的百業營生,大多被魚欄、柴市、火窯把持著。
說白了,咱們都是在幾位東家手底下討生活。
即便你敢打敢拼,混出頭了。
仍然也是被人賞飯吃的……家奴。」
梁老實頓了一頓,用頗為譏嘲的語氣吐出最後兩個字。
白啟心頭微動,這年頭許多人混個溫飽就心滿意足。
賣身進大戶家為奴為仆,也是稀鬆平常。
如果能夠當個穿長衫的管家之流,住在縣城裡面,已算得上很體面了。
像梁老頭這種打心底明白,自個兒只是東家養來看家護院的「打手」。
反而極少。
說白了。
黑河縣十餘萬戶,其中大半想當三大家的奴才。
都還沒門路呢!
「主家高興了,賞你銀子、宅子,甚至幫你張羅娶個婆娘。
可要是惹得主家生氣,讓你下跪、抽你鞭子。
一句話就能奪走你大半生攢下來的家底,也不過反掌間。
阿七,你可曉得老夫為何從一個堂堂二練武夫,淪落到腿腳不靈便,站都難站直的糟老頭?」
借著十幾條鬼紋魚的貴重情分,梁老實難得談起過去的往事:
「早個八九年前,大東家還沒繼承魚欄的生意。
他卡在二練大關,需要一種山貨,名叫『魚龍草』。
得上百年份的熬成水,每天沐浴,用於改易根骨。
老夫當時剛被賞了百兩銀子,一座外城宅子。
遂想著再立一功,報答主家,順便跟楊猛那廝爭奪衛隊統領一職。
我在山裡耐心尋找兩月之久,好不容易尋得一株五百年份的魚龍草。
結果正巧撞上進山來的楊猛,跟他鬥了一陣,最終不敵,勉強逃命。
大東家見到獻上的魚龍草,大喜過望,沒多久就提拔楊猛。
而我受傷太重,又染上毒林的瘴氣,還好命大沒死,只落得一身病痛。
再因為失去突破二練換血希望,直接被大東家下放到東市鋪子,了此殘生。
直到前兩年,我才從一起殺過水匪的老吳嘴裡得知。
我進山的消息,楊猛是從大東家那裡弄來。」
白啟眼皮抬起,扯起嘴角笑了笑:
「主家只重結果。哪個『家奴』尋來的魚龍草沒所謂,關鍵是要看到東西。
這功勞給梁伯你也好,給楊猛也罷,其實都一樣。
畢竟,願意給魚欄辦事效力的打漁人,多的是。
東家養出來的『忠僕』,也不少。
梁伯你這是沒把自己放對位置,奴才對主子忠心是天經地義,沒啥好拿出來說的,放在東家心裡不值一提。」
第三十一章 教頭快刀,熊鷹虎豹
 超級全能學生 一滴神血改變了葉昊的吊絲人生。考試滿分,彩票必中,籃球天才,游泳健將,選一個?不,老子就是全能。美女校花主動跟我表白,霸道女總裁做我知心大姐姐,可愛小蘿莉要我做她的貼心大哥哥。
各位
超級全能學生 一滴神血改變了葉昊的吊絲人生。考試滿分,彩票必中,籃球天才,游泳健將,選一個?不,老子就是全能。美女校花主動跟我表白,霸道女總裁做我知心大姐姐,可愛小蘿莉要我做她的貼心大哥哥。
各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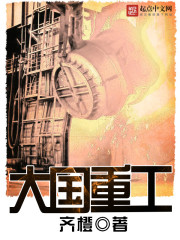 大國重工 冶金裝備、礦山裝備、電力裝備、海工裝備……一個泱泱大國,不能沒有自己的重型裝備工業。 國家重大裝備辦處長馮嘯辰穿越到了1980年,看他如何與同代人一道,用汗水和智慧,鑄就大國重工
大國重工 冶金裝備、礦山裝備、電力裝備、海工裝備……一個泱泱大國,不能沒有自己的重型裝備工業。 國家重大裝備辦處長馮嘯辰穿越到了1980年,看他如何與同代人一道,用汗水和智慧,鑄就大國重工
 重生九零蜜時光 重生軍長掌中寶,身嬌體軟易推倒。身懷空間有靈泉,虐渣治家樣樣好!上輩子受白蓮花迫害,渣男欺騙利用,一世悽慘痛苦。姜小輕發誓,這輩子要用自己的雙手,為家人,為自己,編織出一個錦繡人生!白蓮花想誣
重生九零蜜時光 重生軍長掌中寶,身嬌體軟易推倒。身懷空間有靈泉,虐渣治家樣樣好!上輩子受白蓮花迫害,渣男欺騙利用,一世悽慘痛苦。姜小輕發誓,這輩子要用自己的雙手,為家人,為自己,編織出一個錦繡人生!白蓮花想誣- 我的微信連三界
- 狩屍成癮
- 我是小說里共同的大反派
- 一吻成癮,鮮妻太美味
- 重生原始時代
- 斗羅之諸天抽獎系統
- 我真沒想出名啊
- 修羅戰尊
- 絕世醫聖
- 我的催眠師女友
- 離婚後才發現我被覬覦很久了
- 不熟
- 炎炎夏日,灼灼韶華
- 明星父女
- 重生團寵:影帝夫人又窮又凶
- 四合院:大茂讓我捅婁子
- 女催眠師
- 蠶食
- 亮劍之老子是孔捷